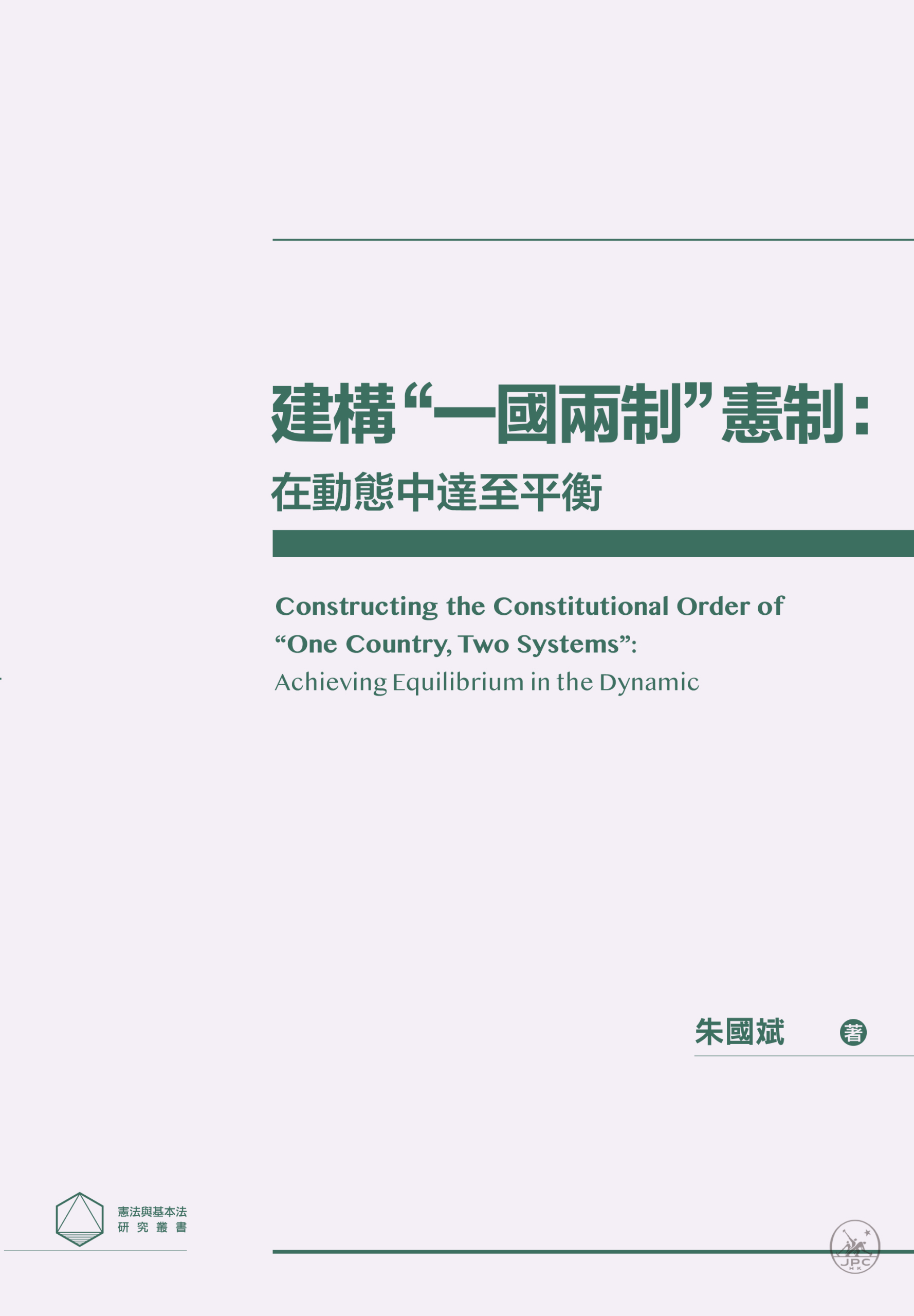建構"一國兩制"憲制:在動態中達至平衡
簡介
本書是朱國斌教授關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香港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文章選集,其中既有學術文章,也有時事評論。學術文章關注的問題既廣且專,其中關於複合制中國、中央在香港政改中的作用、基本法解釋、司法覆核等方面的觀點頗具啟發性。時事評論則保留了作者對香港重大事件的即時看法,是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的寶貴材料。全書中立客觀,緊扣“一國兩制”憲制建構這一中心觀點,尤其追求和堅守香港的司法傳統與核心價值,處處體現了作者對香港的深厚感情和美好期盼。
作者簡介
朱國斌,法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公法與人權論壇主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事事務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比較憲法、香港及內地法律制度、中國人權研究、中國行政管理、地方自治與管治。近年主要著作有《香江法政縱橫——香港基本法學緒論》、《香港司法制度》、《當代中國政治與政府》、《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研究》、《第五次人大釋法:憲法與學理論爭》、《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專論》、Personal Data (Privacy) Law in Hong Kong和Defere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in Judicial Revi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亦有多篇文章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Colo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Human Rights Quarterl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和Hong Kong Law Journal等期刊。
目錄
總序 | iv
序言 | viii
導言
香港當前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對策建議 | 002
第一章 | “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
01 “一國兩制”體現和而不同 | 016
02 “一國多制”下的複合式中國——理論建構和方法論考慮 | 022
03 新憲制秩序與中央—特區關係 | 061
04 從憲法維度建構特區管制的法理 | 082
05 香港特區法院與“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維護 | 093
06 探索“一國兩制”新空間——以“一地兩檢”與“一島兩轄”為例 | 126
07 從ICAC談到香港核心價值 | 153
第二章 | 政制改革與民主進程
01 白皮書著眼香港和國家未來 | 164
02 基本法與特首候選人條件 | 174
03 完善政黨制度 提升管治能力 | 179
04 “獨立”絕非香港的選項 | 184
05 正本清源談《人權公約》的適用 | 201
第三章 | 人大釋法與香港司法
01 香港法院司法審查權的性質、內涵及其實踐 | 208
02 香港基本法第158條與立法解釋 | 244
03 “剛果訴FGH案”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判例法整合制度和落實基本法 | 304
04 “居港權”釋法之理性思辨 | 369
05 人大釋法衝擊香港法治嗎? | 374
序/導讀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關於基本法的研究一直伴隨着“一國兩制”事業的不斷深化而演進。迄今為止,基本法研究大概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 1980 年代初“一國兩制”提出,到 1990 年、1993 年兩部基本法分別獲得全國人大通過,這個階段基本法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把“一國兩制”從方針政策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條款,成為可以操作的規範,最終的成果就是兩部偉大的法典 —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二階段從基本法獲得通過到基本法開始實施、香港和澳門分別於 1997 年和 1999 年回歸祖國,這個階段基本法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基本法文本的詮釋解讀,主要是由參與基本法起草的老一代專家學者進行,也有一些媒體寫作了不少著作,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二是研究如何把基本法的相關條款與政權移交的政治實踐相結合,實現港澳原有制度體制與基本法規定的制度體制的對接,這是超高難度的政治法律工程,最終實現了政權的順利移交和港澳的成功回歸。
第三階段是從 1997 年、 1999 年港澳分別回歸、基本法開始實施以來,基本法研究經歷了一段低谷時間,大家都以為既然港澳已經順利回歸,基本法已經開始實施,基本法研究可以劃個句號了,於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本來已經成立的全國性研究組織“基本法研究會”也無疾而終。 2003 年香港基本法第23 條立法遇挫後,大家才意識到基本法研究不是完成了,而是從實施之日起,故事才真正全面開始。特別是近年來,在國家和香港、澳門有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基本法研究逐漸成為顯學。 2013 年更成立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法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內地和港澳的大學紛紛成立關於基本法的研究機構,基本法研究越來越繁榮。
有人問,基本法研究前途如何?我認為基本法研究前途光明,無論從法學理論或者政治實踐上,基本法研究都是一項長期的偉大事業。美國憲法只有七千餘字,從起草到開始實施以來,美國人和全世界的學者已經研究了兩百多年,今天還在持續不斷地研究,永無止境。各有一萬多字的兩部基本法,需要研究的問題極其複雜繁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基本法研究比單純研究“一國一制”的美國憲法更複雜, 1997 年基本法開始實施才是萬里長征邁出的第一步,漫長的路還在後邊。基本法這本書要讀懂、讀好、用好確實不容易!既然“一國兩制”是國家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的實踐、創新永無止境,那麼,基本法的研究也就永無止境,是值得終身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但是,長期以來,基本法研究存在碎片化問題,成果沒有很好地整合,形成規模效應,產生應有的學術和實踐影響力。這正是編輯出版這套叢書的目的。三聯書店的朋友希望我出面主編這套叢書,我欣然應允。一方面為中國內地、港澳和海外研究基本法的專家學者提供出版自己著作的平台,另一方面也為社會公眾特別是國家和港澳從事基本法實踐的部門和人士了解這些研究成果提供方便。這套叢書的名稱叫做“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叢書”,為什麼加上“憲法”二字?我認為這是必須的,研究基本法一定不能離開中國憲法,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不可能離開國家而單獨存在,兩部基本法也不可能離開中國憲法而單獨存在。基本法不是從天而降獨立存在的法律文件,它們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但絕對不能說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基本法在港澳地方層面具有凌駕地位,超越任何機關和個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無論行政長官或者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或者任何公職人員、市民都要遵守基本法,按照基本法辦事。但是在國家層面,基本法是憲法的“子法”,憲法是其“母法”,基本法的生命來自憲法。如果說“一國”是“兩制”之根、之本的話,憲法就是基本法之根、之本,離開國家憲法來看待基本法、來研究基本法,那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基本法研究就一定會枯竭,而不會枝繁葉茂,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就一定會走樣、變形。我們不能假裝香港澳門沒有憲法,只有基本法,不能誤國誤民、誤港誤澳。“一個國家、一部憲法”,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同樣國無二憲,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具有主權意義的憲法;如果一國有兩部憲法,那就是兩個國家了。既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我們就必須把基本法研究放在整個中國大憲制架構下,根據“一國兩制”的方針,去詮釋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
這才是基本法的本來面目,也才是研究基本法所應採取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不僅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而且也是基本的學術誠實( Intellectual Honest)問題。我們必須以科學誠實的態度,以對國家和港澳高度負責的精神,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去展現事物本來的面目,讓世人看到真相,儘管真相有時讓人痛苦。我們果斷地把“憲法”兩字加上,就是希望把基本法研究放在整個國家的憲制架構和憲法理論體系之下來展開,這樣才真正有可能發展出一套中國憲法關於基本法的次理論體系,才能真正適應香港回歸後憲制的革命性變化,為基本法定好位,為特別行政區定好位,減少無謂的政治法律爭議,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建設特別行政區上。因此這套叢書就定名為“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叢書”。
在這裏,我特別感謝三聯書店(香港)提供的平台,感謝侯明女士和顧瑜女士的大力推動,讓海內外研究基本法的專家學者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出版渠道,及時發表自己的著作,為憲法和基本法的實踐、為繁榮“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學術研究做貢獻。
王振民
2017 年 7 月 4 日於北京
序言
一、“一國兩制”是一種新的憲法制度
香港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三大憲法性原則之下制定的,它確立了中國憲法下的又一種新型地方制度和又一類新型中央─地方關係。
“一國兩制”首先是作為一種思想、方針和政治理念提出來的,是一種問題解決方案。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此先後都有過論述。“一國兩制”同時又是一種新的憲法制度或憲制( Constitutional System),即由憲法確立的一種基本國家制度,其下的中央地方關係就是一種新型的憲法設計( Design)和建構( Construct)。既然如此,“一國兩制”就不是、更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說“一國兩制”下的中央地方關係是一種新型的憲法關係,是指在此關係結構( Relational Structure)之下,第一,中央與特區開始了一種新的關係,這是相對於業已存在的中央與直轄市、中央與省、中央與自治區的關係而言;第二,新的關係下的制度性安排與內涵不同;以及第三,新的關係下中央與特區各自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互動原理和方式不同。
二、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一國”解決的是國家統一問題,即“和”。“和”就是統一與和諧。“兩制”要求維持內地與香港的“不同”。所以,“和”而“不同”就是既有國家主權的統一與唯一,又有地區制度之分別;既維護國家憲政制度的一體,又保持不同地區制度運作的相互獨立。就此而言,“一國兩制”就是要體現和而不同。
“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簡單割裂“一國”與“兩制”失之偏頗。我以前就曾寫到:“‘一國’解決的是主權,‘兩制’解決的是治權或說管理權。‘一國’指的是擁有全部主權的中國,因而排除了各種形式的以分割或共用主權為目的的國家結構和政府形式。我著重指出這點,意在指出企圖以‘兩制’之特殊性來排棄‘一國’之根本性的任何行為在政治上和法理上是不能接受的。”“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的產物和化身,是國家在國內行政區域和地方制度上的特殊設計和精心安排。它解決了中央與地方關係,提出了新型的關係模式,它同時為特區政府的管治提供了基調和發展空間。特區與內地的區別在於:它實行資本主義,它比其他地區行政單位享有更高、更多的自治權。”“正因為有如此充分的政治空間、自由的經濟環境、和高度的行政自治,故而有港人經常眼裏只有‘兩制’而沒有‘一國’的概念,或者經濟上要‘一國’,政治上要‘兩制’。”這當然是絕對不正確的。
也要看到,近些年來,也有一些內地學者置“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之原意而不顧,片面地以“一國”之名試圖排斥、蠶食、攫取特別行政區之自主權,壓縮特區自治權空間。這在憲法與基本法理論上是不可取的,實踐上也是達不到積極效果的,甚至還會帶來港人情緒上的抵制和反抗,其實是得不償失。
三、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已經二十二年有餘了,再過兩年就走完了“五十年”的一半。這二十多年來,特別行政區一路走來可謂困難重重,步履艱難。“一國兩制”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失衡”情況和矛盾狀態。有學者認為,“這矛盾的根源來自雙方在歷史背景的、生活經驗的、思維方式的、行政傳統的、法律體系的和核心價值取向的差異。”這種理解還是有道理的。鑒於“一國兩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一路上風風雨雨、磕磕碰碰也是意料之中的、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失去信心和動力。
2015 年 12 月 23 日,當時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北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習近平指出,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他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指出: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才能推動“一國兩制”事業行得穩、走得遠。這明確表明了中央政府對實踐“一國兩制”的態度,無疑堅定和提振了我們對“一國兩制”這一憲法制度和特別行政區未來的信心。
四、尋求“一國兩制”的動態平衡發展
從制度設計的本義上講,“一國兩制”應該在根本原則和建構不變的前提下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這包括具體制度的調整、充實和完善,此即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成長。同樣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良性發展更取決於“兩制”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戰略性認同和策略性包容。這些年來,中央與特區的互動以及“兩制”之間的關係遇到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有人大常委會釋法( 1999)、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2003)、以爭取“雙普選”為目標的“雨傘運動”( 2014)和欲罷不能的“反修例運動”( 2019)等。儘管它們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波蕩和震動,整體上仍然是發生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
“一國兩制”如何健康發展,並行穩致遠?首先,雙方必須真誠認同“一國兩制”不是急就章,不是權宜之策,而是立足高遠的長遠之計,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性抉擇,是實現國家統一的重大制度性設計。其次,“兩制”之下的中央和特區須持相互策略性包容態度,在各自活動範圍內不能動輒指責責難,更不能懷有隨時企圖侵佔對方權利和利益的居心。堅持底綫思維,對特區一方而言,“底綫”就是不能冒犯“一國”原則;對中央而言,“底綫”就是維護“兩制”的長期存在。現實中,“兩制”不時地試探和摩擦是正常的,如此可在動態中達至一種平衡狀態。這當然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
有觀察者敏銳地看到:“‘一國兩制’未來能否平穩發展,首先取決於未來雙方對於對方的政治體制能否恢復或提高戰略性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未來戰略走向,取決於中國當政者未來對大陸道路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戰略選擇。”“如果戰略性認同不能恢復或提高,那就只能取決於雙方的策略性寬容能否得到維持。如果雙方既缺乏戰略性認同,又不能維持策略性寬容,必然會導致衝突加劇,‘一國兩制’之路也會充滿崎嶇坎坷。”不得不說,這是一種非常現實主義的觀點,儘管比較悲觀。
在剩下的歲月裏,我們當然希望看到更多的是“兩制”的良性、積極的互動,並在運動中尋求共識,達至動態平衡。
五、“五十年不變”,那麼 2047 以後呢?
大約在 2017 至 2018 學年的第一個學期,在我的“香港憲法”(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課堂上,第一次有年輕的學子問到 2047“大限”這個仍在休眠中( Dormant)的問題。這班學子當時年約二十左右,三十年後即 2047 年大約五十左右,正當壯年。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就表明他們在關心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和他們在特別行政區的未來。
這是一個大問題,其實首先這不是一個純粹法學的問題。若用規範法學方法回答他們的話,他們可能會更加迷茫或失望。我們總不能簡單地回答: 2047 年,“一國兩制”結束,“一國一制”開始。
我的理解是,“一國兩制”絕非權宜之計,而是中國執政黨領導人長時間深思熟慮的成果。若從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的思想脈絡來看,這是一項根本國策,應該是長期不變的。鄧小平說:“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他又說:“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時至 1988 年,鄧小平還在說:“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後是不需要變。”我們聽得出、看得到,鄧小平講這些話時信心十足。 1990 年 4 月 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香港基本法,以憲法性法律確認了“一國兩制”,那麼作為憲法制度的“一國兩制”應該是著眼於長遠的設計和建構。對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思想路綫和憲法與基本法共同確立的憲法制度,我們應該自始至終地保持一種戰略性認同。
六、關於本書
自 1995 年始,我就服務於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從事教學與研究。自 1996 年開始,我先對碩士生、後對本科生講授香港基本法,直到目前為止。我以一個學者的視角,一直觀察與研究“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實踐。“一國兩制”是一項新鮮的憲法制度,基本法實踐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領域。
前前後後,我寫作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這包括獨著、合著、學術論文、著作章節、政策性專業性雜誌文章、報刊文章等。 2010 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論文集《香江法政縱橫─香港基本法學緒論》,收錄了我個人獨自在 2009 年前發表的學術雜誌文章與報刊文章。
《建構“一國兩制”憲制: 在動態中達至平衡》選擇性地收錄了我 2010 年以後發表的部分學術性雜誌與報刊文章(個別文章除外) ,其主題就是觀察與探討“一國兩制”這一新憲法制度的生成與發展。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包括對複合式中國進行一種理論建構和方法論考量,建構新憲制之下的中央與特區關係以及特區管治的法理。第二部分專論政制改革、選舉與民主進程,特別是特區政改中中央的權力及其主導作用。第三部分研究基本法下的人大釋法制度及其與香港司法制度的互動。三部分收錄文章基本緊扣著“一國兩制”憲制建構這一中心主題。
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是多方努力的結果,特在此記錄如下:首先,李浩然博士向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慷慨舉薦本選題。然後,三聯書店策劃編輯顧瑜博士真誠接納並作出編輯安排。之後,編輯蘇健偉先生在閱讀我 2010 年後出版的所有文字後提出了恰當的編輯與製作建議。值此之際,我要特別感謝以上各位。與此同時,我希望記錄我對我同事袁鳳英( Kris)小姐的衷心感謝,她幫助我彙集編排了散見於各處的文字,費心費時費力。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是一份不間斷的工作,也是一項有意義的事業。真心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對基本法學術研究作出哪怕一丁點的貢獻。
朱國斌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樂耘齋
九龍塘 香港
2020年1月10日